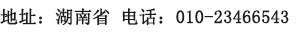文/斯舜威
诗人、中国美术学院视觉中国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王良贵,于4月6日下午在淳安去世。美院、诗歌圈不少人士纷纷表示哀悼。
王良贵,年生于浙江淳安。他出版过长篇小说《地点上的人物》(百花文艺出版社,年),诗集《幽暗与慈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年),诗集《火的骨头》(中国人口出版社,年)。
前浙江美术馆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斯舜威在年6月曾为王良贵撰文,当时王良贵已在病中。斯舜威任《美术报》总编辑时,曾邀请王良贵担任副刊编辑。经斯舜威先生授权,小时新闻全文转发。
“凡有过的一切/我过目不忘/凡记下的一切/用于辞别/山谷中云烟飘散/人最终死于心愿/是一年年冰雪消融/难舍难分。”这是王良贵《辞别》中的句子,读来颇觉沉重。良贵的诗大多是沉重的,因为他的生活一直并不轻松。
这首诗写于年10月11日,是他“诗三百”的“压轴之作”。时隔5年,当我惊悉他正缠绵于病榻,与病魔作顽强抗争时,诵读这样的诗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于庚子年初出游,一直滞留于遥远的南半球。我的好友、出版人彭明榜和我微聊,告诉我:“我接到一部诗稿,作者你认识。”我问是哪位,他回答:“王良贵。”我说:“当然!《美术报》老同事啊。”于是,明榜兄简要讲述了几位朋友如何“接力”似地把书稿转到他手里的情景。
“一传手”是画家杜觉民,我的同庚好友,良贵的知音,良贵的诗集《幽暗与慈悲》的所有插图,都取自杜觉民的水墨作品《众生》系列。杜觉民的画也是让人感到分外沉重的那种类型,诗和画真正的珠联璧合,那是缘于心灵的相通。
杜觉民也正滞留于域外。我和他微聊,他告诉我他和良贵多年前初交时的一段插曲:那时良贵在《美术报》编副刊,杜觉民也尚未闯荡京城,他欣赏良贵之才,深知良贵活得艰辛,有意不动声色帮一把,便不经意地问:“良贵,你喜欢画吗?”这句话其实是杜觉民准备送画的“前奏”,没料到良贵居然不接茬:“我不懂画,也不喜欢。”杜觉民送画的“脚本”便进行不下去了。后来,良贵在报纸上发了自己的诗,并配了杜觉民的画。杜觉民看到了,觉得好奇,便打“良贵,你不是不懂画吗?怎么选了我的作品作为配图?”良贵说:“你的画我懂的。”这样的散淡之交,我觉得非常纯粹和美好。据我所知,良贵其实一直用一种近乎刻意的“防守”,小心地呵护自己的尊严。
(杜觉民插图选载)我的思绪,跳跃到了20年前。那时,我接任《美术报》总编不久,雄心勃勃,版面不断“扩容”,从4开4版扩到了8版、16版、24版,乃至48版,人手不够,便“收编”了不少社会上的“散兵游勇”。当时,受用人制度限制,要想录用体制内人员非常困难,我们就打破条条框框,直接聘用社会上那些不需要正式编制、不需要办理繁琐手续的“杭漂一族”。杭州是书画重镇,“体制外”的书画人才特别多,《美术报》便向他们敞开大门,一时间可谓群贤毕至。
王良贵就是其中的一员。
良贵加盟《美术报》,缘于人物画家王犁的举荐。俗话说“英雄不问出处”,良贵属于“另类”,论学历,他只有中专文凭,论专业,他是学机械的,但我看了他写的诗歌和文章,大为欣赏,觉得他文字功底非常好,人又非常实在,他当时漂泊无着,我觉得应该给他一个支点,看看他能否撬起“地球”。
初到西子湖畔的王良贵,如此这般向朋友介绍自己的故乡:“千岛湖,比保俶塔塔尖还要高出两百米”。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地理上的落差,我知道王良贵的话语里肯定包含着更深层次的感慨万千。淳安和杭州的“落差”,自然不止于此。遥想当年顾况慨叹“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待看了白居易的诗之后才表示“道得个语﹐居即易矣。”而杭州,何止“米贵”?杭州在人文版图上的居高临下的优势,何止高出淳安“几百米”?王良贵会写诗,但要融入杭州,谈何容易?
良贵的家乡在淳安县威坪琴川。淳安素称穷乡僻壤,琴川则是“穷中之穷”。同样出生在淳安的王犁告诉我:“琴川在浙皖交界处,相当偏僻,比一般的淳安人要更困难一些。”我记得多年前供职于浙江省民政厅的一位作家写过一本反映新安江水库移民的书,书中描述的淳安农民的生活状况之窘迫,是很难想象的。王良贵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读初中要翻越3座大山,一罐咸菜要吃一个星期、甚至半个月。他的成绩却是出众的,初中毕业就考上了南京的一所专业学校,堪称奇迹了。农村里能够考上初中中专的都是佼佼者,如果家境许可,继续读书,高考摘冠是轻而易举之事。然而,对王家来说,能够让几个孩子中的一个跳出农门,已属上上大吉。然而,少年良贵没有满足,他有足够的多余的精力和精神,游离于“机械”之外,驰骋于诗的天空。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成为一个诗人的原因,至少有一点,在他此后的生命历程中很少能够看到“机械”的痕迹,却与诗歌难分难舍。我不知道假如他考上的是大学中文系,此后的生活道路将会怎么样?
良贵中专毕业后就回到家乡一个小镇的一家小厂就业,那个小镇唯一的一条街道只有短短几十米,良贵很清楚一个来回有多少步,因为下班后他常常在寂寞的街上踱来踱去。一次难得去县城,他发现几个壮汉在殴打一个妇女,便挺身而出,仗义执言,遭到围殴,打成重伤。后来施暴者固然受到了法律的惩罚,良贵也付出了见义勇为的“代价”。没多久,小厂倒闭了,他又在县城的一家小厂上班,不久又倒闭了,他便去厦门台资企业打工,未几,又铩羽而归。我猜想,如果王良贵没有外出读了几年中专,没有学会写诗,那他很可能会像其他同村青年一样成为一个除了打工别无所求、除了养家糊口别无奢望的“农民工”,就如同他老实巴交的父亲一辈子是个建筑工一样。然而,一旦他怀里揣上了一个“梦想”,他注定要走出琴川,闯荡世界。
于是,他赤手空拳闯进了杭州,他唯一的“武器”,便是一支写诗的笔,和一身山里人的勤劳与质朴。他的笔,便是他的“琴”。他是琴川之子,他要用他的“琴”,弹奏琴川的故事,弹奏他的心曲。
王良贵到报社不久,便在埋头苦干中显露出他的人品和才华。我曾在一次编前会上恳切地说:“王良贵的诗,连我这个中文系毕业、八十年代就发表诗歌的中国作协会员也写不出来。”这无意中的褒奖,据说对良贵产生了很大的心理震荡,他也由此对我产生了“知遇之感”。
王犁无疑是王良贵的第一个“伯乐”。这位曾经的淳安美术青年、中国美术学院学子,现在的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人物画家,还在美院读书时,偶尔从家乡的《千岛湖》杂志读到一组诗歌,大吃一惊,心想:“王良贵是谁?淳安居然有能够写出这般诗歌的人才?”于是,他回到家乡,慕名找到了正下岗在家的王良贵,遂成莫逆之交,良贵在县城小厂的那份工作,也是王犁动用父亲和县领导的关系找到的。
身处杭州,王良贵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曾坦言“看清命运的落差和无法回头的走势”。他给我的印象有两点:一是近乎谦卑的质朴,二是近乎忘我的勤勉。事实证明,这两点已经深入骨髓,贯穿始终,他由此也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人的理解和尊重,也赢得了更多的“伯乐”的器重,乃至后来居然踏进了中国美术学院高高的门槛,成为院办秘书、秘书科长,乃至走上了处级岗位。
我没有询问他到杭州初期是如何艰难度日的,但我看过他的自传体小说《地点上的人物》,知道那就是他的自我写照,由此深感生活的艰辛,“杭漂”的不易。《美术报》的聘用薪酬是菲薄的,恐怕连房租都不够,但他却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死心塌地投入其中。当时集聚的那批“散兵游勇”,有不少在书画界小有名气,颇有影响,他们可以借助于《美术报》的岗位优势获取一些薪酬之外的精神和物质补偿,但不搞书画的王良贵则没有这份便利了,他却丝毫没有计较,让他干校对,他欣然从命,他曾愉快地自嘲为“校书郎”,版面不断增加,薪酬一分未加,他毫无怨言。有一次搞“书画双百家”的大型活动,突击出了几百个版面的“号外”,大部分都是他校对的,现在想来很惭愧,居然没有关心他是否来得及,他也这样扛下来了。我接任总编后,出于改版需要和个人喜好,新辟了“美术副刊”,且由我亲自编辑。良贵来了不久,我就把这一块交给了他,由他担任副刊编辑。这次和王犁交谈后才得知,这对他是莫大的鼓励,让他信心倍增。在他看来,从淳安的琴川到杭州西子湖畔,他终于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已经退休赋闲的我由此也颇多感慨,深感担任一定职务的人,大胆识人、用人,放手让他们去干,是多么重要。
我留意到王良贵诗集中九十年代中期是他的初始期,也是爆发期,应该也是生活上、工作上的迷茫期。他的诗歌似乎受到海子较多的影响,他在杭州逐渐扩大影响,靠的还是他的诗。王犁曾帮他牵头在“枫林晚书店”搞了一次诗歌朗诵会,请来了好几位与王良贵素不相识的杭城诗歌界的大腕,他们对良贵的诗高度认可,也由此而对良贵刮目相看。大型文学杂志《江南》随后刊登了他的一组诗歌,又刊登了他的写打工生活的一组《地点上的人物》。这几篇纪实小说,被远在天津的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敏锐地发现了,就约他继续写,写一本书。那时他就在《美术报》,他的岗位,白天是忙得不亦乐乎的,只能熬夜,用一根根几元一包的劣质香烟当“助燃剂”。“如果作为一条狗,在不平静的夜晚它忍不住要狂吠;作为一个苦闷而空洞的男人,他的口袋需要装一包两块钱的香烟,这就是我与诗之间的关系。”这是王良贵的自白,也是真实写照——
让我点燃一支香烟
火站了起来
我看见,火的骨头
这是良贵《叹息与荒凉》中的句子,这句子有着让人震颤的穿透力。良贵写诗,好几处用到了“骨头”的意象,如:
“燃烧的总是事物的骨头
干燥、内部充满风的骨头”
“它终究要指向既有的事实,骨头的气味
说出一个方向,同时说出全部”
“木头的定义就是骨头/从来不曾有过血肉”
良贵的“意象库”里,“刀”也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