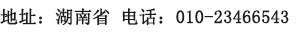年3月的一天,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内的工作人员正在像往常一样紧张有序的工作着,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办公室的宁静。
工作人员接起了电话,电话那面的人先是礼貌的同大使馆工作人问候了几句,紧接着说明了自己此次来电的原因。
在了解了基本情况以后,工作人员便将这一事项向上级进行了汇报,可是谁都没有想到,这样一通看似普通平常的电话,竟然惊动了中国驻德大使吴恳。
吴恳亲自询问了来电人员的身份与具体情况,得知来电的人是一名德国的医生,因为自己和家人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新冠肺炎确诊症状,他才不得不求助于中国政府,希望能够从我国得到有效药品以及防护物资方面的援助。
图中国驻德国大使馆
彼时,新冠肺炎正在欧洲肆虐,身处旋涡中心的德国形势更加严峻,有效药品已经断供,医院内有效的防护用品也已告罄,想要获取治疗只能靠病人自己另找途径。
所以,走投无路的他想到了中国这位“老朋友”。
而中方的反应也并未让他失望,在收到他的求助后不久,中国驻德大使吴恳便立即同国内取得了联系,并与的一家浙江的药企达成协议,答应给这名德国医生无偿赠药。
南京市政府听说了这件事情,也立马自发的筹集了瓶抗疫药品和多套口罩、防护服等稀缺物资,同样无偿捐献给了这位德国医生。
这些救命物资经过长途跋涉以后顺利地抵达了德国机场,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又立即马不停蹄的将物资送到了多公里以外的目的地,第一时间送到了德国医生的手中。
图满载防疫物资的飞机
同时,使馆的工作人员还向这名德国医生传达了南京人民最亲切的问候。
可能中方的一系列操作让人不免感到有些疑惑,因为彼时的中国也在忍受着新冠肺炎的困扰,国内的情况虽然没有国外那样严重,但是仍旧不容乐观。
这位德国医生究竟有什么特殊的身份能够让中国如此尽心竭力的处理他的求助呢?他有什么特别的贡献能值得全体南京人民问候关心呢?
这件事情还要从他的祖父说起。
这名德国医生叫做托马斯·拉贝,说起他来可能很少有人知道,但是他的祖父一定有很多人听说过,尤其是南京人民,相信一定都对他印象深刻,他就是约翰·拉贝。
图约翰·拉贝
约翰·拉贝曾经救过中国整整25万人民的性命,还是在中国最艰难、最孤立无援的时刻。
(为了方便读者记忆和区分,下文中求助者德国医生托马斯·拉贝一律用“托马斯”称呼,他的祖父约翰·拉贝一律用“约翰”指代。)
一个外国人的担当
年,约翰出生在德国汉堡,年幼丧父,约翰·拉贝的童年时光过得凄惨而又暗淡。
初中毕业以后约翰便被迫放弃学业四处谋生了,他在德国的许多城市都曾留下过足迹,还曾在非洲颠沛流离。
图青年时期的约翰·拉贝
年,26岁的约翰来到了中国,此后的30年,他都是在中国度过的。
起初,他在位于北京的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华机构工作,在这期间,他还与自己的未婚妻多拉结成了伴侣。
年11月,约翰被调任到南京,这座他亲手创造了奇迹的城市。
刚刚来到南京的约翰生活很是惬意,因为他外国人的身份,不管做什么,都会享有一定的特权。
广州路小桃园10号有一栋美丽的西式小洋房,那里便是约翰的住处。
图拉贝故居
红瓦白窗,在当时的南京显得是那么的格格不入,房子的后面更是有一片极大的花园,里面种满了各种各样名贵漂亮的花卉,春天一到,就像是天堂一样。
走进洋房,处处都可以看到主人的巧思以及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一楼是用来接人待客的客厅,客厅的墙壁上挂满了动物的皮毛及兽角等装饰品,那些东西都是贝拉年轻时自己亲手狩猎得来的;
清晨阳光会透过可升降式的大窗户照进客厅中来,给客厅内的物品镶嵌上毛茸茸的金边,就像是一幅画一样。
顺着楼梯向上走,二楼是一个小阁楼,站在阁楼里,可以俯瞰南京全城,望见中山陵的蓝瓦灰墙。
图拉贝故居内部
当然,最让约翰觉得开心的是他的小孙女十分喜爱他的家,尤其喜欢那片种满花草的大花园。
约翰在这里生活了七年的时间,这七年也是约翰一生中最快乐、最难忘的一段时光。
卢沟桥事变的一声枪响,将中国人民彻底推进深渊的同时,也打破了约翰快乐、安宁的时光。
日军的飞机开始轰炸南京,流离失所的人民为了保命开始四散逃走,南京城内的外国侨民也纷纷撤离。
彼时正在北戴河度假的约翰也听到了南京被轰炸的消息,德国大使馆也给他发来信件,奉劝他快些撤离,猖狂残暴的日本侵略军甚至直接发出最后通牒,警告约翰这样的外国人快些离开,否则后果自负。
图卢沟桥事变纪念油画
一开始,约翰也是要走的。
他只是一个没有什么能力的外国人,自己的生存还要仰仗着国家赐予自己的身份,他能做什么呢?他应该像其外国人那样,拍拍屁股走掉就可以了,又安全又简单。
可是真正要动身的时候,约翰又犹豫了,毕竟他已经在这里生活了30年啊!他在这里受到的善待比他过去的人生加在一起还要多,这里的人们真的单纯又质朴。
事变发生以后,有能力的人早就逃走了,剩下的都是手无寸铁的贫民百姓,如果他也这样不负责任地离开,那么剩下的人下场会是怎么样的呢?
尤其是在看到日本侵略军做出空袭、奸淫掳掠、杀人放火等等恶行之后,约翰开始动摇了。
图约翰·拉贝与妻子合影
约翰将自己痛苦的抉择都记录在了日记中:
“今天,善待了我30年之久的我的东道国遭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富人们逃走了,穷人们不得不留下来,他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他们没有钱逃走,他们不是正面临着被集体屠杀的危险吗?我们难道不应该设法帮助他们吗?至少救救一些人吧,假如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呢?”
抉择这在一瞬间。最终,约翰决定留下来。
打定主意以后,约翰便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筹备工作,首先,他留下来的目的便是为了救人,那救人一定要有一个安全的场所,所以他就在自家院子挖了一个防空洞,并在上面盖了一面巨大的纳粹党党旗。
图拉贝故居的防空洞
如此,不管是空袭还是冲进人来,都不能伤害到防空洞里面的人。
约翰是一名纳粹人员。年3月,为了解决自己所创办的学校的经费问题,拉贝加入了纳粹党,后又担任了纳粹党南京地方小组的负责人。
其实这个身份对他来说有利也有弊,不过在这一危难时刻还是好处更多的,它帮助约翰保护了更多的中国人。
渐渐的,来拉贝家躲避空袭的人越来越多,小桃园10号也不再是那个充满欢声笑语吃的小洋房,而是成为了一个充斥着不安、庆幸、担忧等等复杂情绪的了“西门子难民收容所”。
图拉贝故居的约翰雕像
同年11月开始,国民政府开始撤离南京,南京人民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
好在,有20几位和约翰一样的人站了出来,医院的医生和在金陵大学任教的传教士,他们找到了约翰,计划一起联手保护南京市民。
他们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由约翰担任主席。
约翰家后院那个小小的防空洞早就已经不够用了,想要保护更多的人,他们必须想办法在南京划定一块区域作为安全区才行。
“安全区”的提出很快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同意,不仅如此,中国政府还承诺将为约翰他们的国际委员会提供必要的现金、粮食和警察。
图南京大屠杀的惨烈景象
可是即便约翰承诺安全区是绝对中立的,只有非战斗人员可以躲到那里去,暂时性的躲避城市炮击,可是仍旧遭到了日本方面的拒绝。
经过约翰等人多方面的努力,日本才勉强同意只要里面没有中国军队驻扎,他们便不会攻击。
春节时的礼物
年12月13日,约翰在再次被轰炸声警醒,这对中国人民来说早已习以为常的声音,对于约翰来说,仍旧每一次听到都是胆战心惊。
此时的约翰心中十分清楚,南京将在不日之后沦陷,他必须抓紧时间,为日本人进城以后的安全区安全做好准备。
图电影《拉贝日记》剧照
当天下午,约翰高举着印有安全区徽章的旗帜,带着秘书史密斯去和进城的日军交涉。
经过漫长的商议谈判,日本特务机关负责人原田熊吉终于允诺:安全区人口将由日军派兵驻守,区内可留警察,除警棍外,不准携带武器;安全区委员会可享用存米1万担,并可将安全区外的存米运人。
“那被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能否依照国际法保全性命呢?”约翰追问。
对此,原田熊吉并没有给出回应。
很快,日本侵略军便闯进了武汉城内,对于那段记忆,尽管多年以后,约翰每次想起仍旧觉得胆战心惊。
图日本军强迫中国人做苦力
“日本人占领城市后,日本军事当局像是失去了对部队的控制,军队进城后进行抢劫达数周之久,约有2万名妇女和姑娘遭到强奸,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惨遭杀害……”约翰在信中2写到,他的话也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用作呈堂证供。
安全区外的人民每天都生不如死、胆战心惊,约翰看到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十分痛苦:
“整个城市约有三分之一被日本人纵火焚毁,时至今日,纵火事件还在连续不断地发生。城市里没有一个商家店铺未遭到日本人的打砸抢。整座城市,被枪杀的或被其它方式处死的人暴尸街头,随处可见,日本人甚至禁止我们硷尸安葬……”
图青壮年被押往城外集体绞杀
而约翰更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此前,为了保证安全区能够为南京人民提供一定的庇护,约翰与日本方面交涉了许久,可是南京沦陷以后,不守信用的日本人却时时刻刻都在威胁着安全区的安全。
就连约翰的小洋房都是一样,约翰在家的时候日本军还会有所收敛,而一旦约翰不在家,这里便会成为凶杀案的现场。
为此,约翰不得不每天都守在收容所旁,为保护难民做出一些微薄的力量。
图侵略军在安全区内搜捕青壮年
“今天我得亲自站岗,也就是说,我必须注视着自己的难民收容所,双眼盯着我家后面德国学校里的名难民和我家前面中学里的名难民。如果日本人强行闯人,我虽然阻挡不住,但我起码可以做一个目击者,观察事态发展以向世界通报。”
在给妻子的信中,约翰如此写到。
南京大屠杀期间,仅仅约翰亲眼所见并记录在案的惨案,便多达多个。
约翰设法为难民争取粮食,每天辛苦工作,导致他的身体越来越差。
图《拉贝日记》剧照
原本约翰便患有糖尿病,加上每天只能睡不到四个小时,糖尿病经常发作,约翰痛苦不堪,他似乎觉得自己的生命都已经要到尽头了,可是他的心愿仍旧是在去世以前拯救更多的无辜百姓。
年1月31日,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按照以往来说,这一天是一整年来最热闹、最开心的一天,可是今年似乎有些不一样。
“西门子难民收容所”的难民们今天都早早的便起来了,不过不是忙着贴对联嗑瓜子,而是制作一面巨大的横幅。
约翰起床以后,院子里的难民便举着横幅排着整齐的队伍向他行三鞠躬礼,横幅上写得是中文,约翰有些看不明白。
图《拉贝日记》中,约翰正与难民待在一起
“YouarethelivingBuddhaforhundred-thousandpeople.”一位中国学者帮约翰翻译了过来,“你是几十万人的活菩萨。”
“这样的赞誉我可承受不起。”约翰赶忙拒绝,他甚至怀疑是不是学者翻译错了。
得到的答案却是:“我所念的,字字准确。”
这样的盛赞落到约翰的耳中,带来的并不是光荣和满足,他甚至都不敢看那些难民们感激而又庆幸的目光。
因为约翰要离开了。
图保护难民的约翰·拉贝
他实在妨碍日本侵略军太多了,他身后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将要被迫改组,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安全区也要被迫解散,就连他自己,也被要求即刻回国接受质询。
他不知道要怎么样跟众人说,因为自己离开,将要意味着他们唯一的庇护所也将消失,他们将重新被赶回到敌军的剪刀下去,那他们将如何生存呢?
约翰陷入了自责。可是对于中国人民尤其是南京人民来说,约翰做得已经够多了。
在南京沦陷之初最危急的两个多月里,安全区共庇护了25万中国难民,受到庇护、幸免于被日军蹂7的妇女有数万人,仅拉贝家就收容了多名难民。
图《拉贝日记》剧照
在中国孤立无援、腹背受敌的艰难时刻,是约翰,这个同中国没有任何关系的外国人保护了他们,不眠不休、不求回报,这样的情谊,对中国人来说实在是太宝贵了。
约翰晚年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约翰离开的日期已经定了下来,就在年2月22日。
约翰离开的这一天,码头上人山人海,大批大批的南京市民从藏身之处出来,冒着生命危险亲自为约翰送行。
抽泣的声音、祝福感谢的话语、不舍的挽留交织在一起震耳欲聋,约翰看着送行的人群,不断的劝着他们快些回去。
图《拉贝日记》中万人送行的场面
离别的时刻还是来了,约翰登上了船,跟南京人民挥了挥手,离开了这座他生活了多年的土地。
离开中国以后,约翰一直致力于让世界人民看到日本在华所犯下的罪行,他的日记和他所拍摄的照片,成为了谴责侵略者最有力的证据。
可是很快,他便被勒令必须从此对在南京发生的一切保持沉默,他辛辛苦苦拍摄的照片也都被收缴,约翰对纳粹党彻底失去了信心,他提出退党,可是却遭到了拒绝。
约翰的晚年并不安顺,仍旧饱受着战争之苦。
图拉贝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部分成员合影
年11月,他在柏林的住宅在大轰炸中被毁。
又因为他没能从纳粹党中退出,所以年5月,苏军攻克柏林后,约翰先后被苏联和英国逮捕,同盟国的法庭一直视他为纳粹分子。
彼时的中国作为战胜国终于不再任人宰割,有能力出手报答他了,中国方面在了解到拉贝的情况后,为他寄去了多份担保信件,并提供了大量证据以证明他在南京的贡献帮助他洗去了纳粹的罪名。
而这个时候约翰已经63岁了,饱经风霜的他在此时看起来就像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
同时,约翰的生活条件十分不好,全家六口没有任何收人来源,只能靠收集野菜、橡子做成面糊汤勉强度日。
图《拉贝日记》旧照
约翰的情况几经辗转传到了中国,南京立即成立了相关的机构,为约翰筹集救济金,帮助约翰度过难关。
时任南京市市长沈怡也捐出了自己一个月的薪金作为表率。救助约翰的劝募委员会不久便募集到法币1亿元,经特别批准,兑换成美元,辗转汇给了拉贝。
由于当时的柏林有钱也未必买得到食物,沈怡又紧急派人在瑞士购买奶粉、香肠、茶叶、咖啡、牛肉、果酱、奶油等食品,打成四大包寄给拉贝,并决定从年6月起,每月给拉贝寄赠食物一包,使老人在晚年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图《拉贝日记》剧照
尽管当时中国尚处在战乱之中自顾不暇,但是还是纷纷伸出手,报答约翰的恩情。
可是我们能在生活上给予约翰相对的帮助,可是却无法组织战争的脚步,柏林危机爆发,约翰所在的西柏林沦为孤岛,约翰就这样在战乱与动荡中与世长辞。
他的离世几乎没有人知晓,因此也没有人为他举办任何形式上的悼念活动。
他孤零零的坟墓前只立着一个简单的墓碑,上面写着:“一个好人,一个不屈的人,约翰·拉贝。”
图约翰·拉贝墓碑
其后代与中国的联系
约翰逝世后几十年,他的故事似乎被国际社会所忘却了,直到年,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南京大屠杀纪念大会上,约翰的外孙女乌苏拉首次向外界公开了约翰多页的日记副本,立即引起轰动。
约翰的日记也成为了南京大屠杀最重要、最翔实的史料之一。
如今,南京市鼓楼区广州路小粉桥1号伫立着一座德式小洋楼,那里便是约翰·拉贝的故居。
过去,这里曾经保护了超过六百名中国难民,现在,每天都有许多人到那里去缅怀悼念。
图拉贝故居
年9月,约翰的外孙女乌苏拉重回阔别了半个多世纪的南京,站在熟悉的外公的房子前,她流下了眼泪。
她记得,这里有她最喜欢的后花园,以及再也回不去的、有外公陪伴的快乐时光。
在德国海德堡,约翰的长孙托马斯建立了一个旨在促进世界和平的约翰·拉贝交流中心,中心的网站使用中、德、英、日4种语言显示。
年8月,在德中国留学生及旅德华人为中心捐献了一尊拉贝的小型半身青铜塑像,塑像底座上写着“南京好人”4个字。
图约翰·拉贝纪念雕像
年,时任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访华时,特意前往南京,在建于西门子公司原址上的拉贝纪念碑前默哀。
约翰留给后代的财富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托马斯意识到了病毒带来的威胁,他每天都和中国医生友人保持沟通,了解疫情进展,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受到了中方最快速、最大度的帮助。
“感谢中国人民在我和我的家人最需要的时候帮助我们”,托马斯说,“我们将永远感恩”。
托马斯虽然从未见过祖父,但是丝毫不妨碍约翰在他心目中的英雄形象,他对这样一位素未谋面的祖父,始终充满骄傲。
图约翰拉贝故居内展品
看着南京的发展越来越好,托马斯也觉得非常高兴,他觉得如果祖父能够看到今天的南京,那他一定会非常的满足自豪。
“80多年后,中德友人之间这种守望相助的情谊仍在延续……这些故事,每天都在感动我和我的同事们。”中国驻德大使吴恳如是说道。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便是大国风范!
-完-